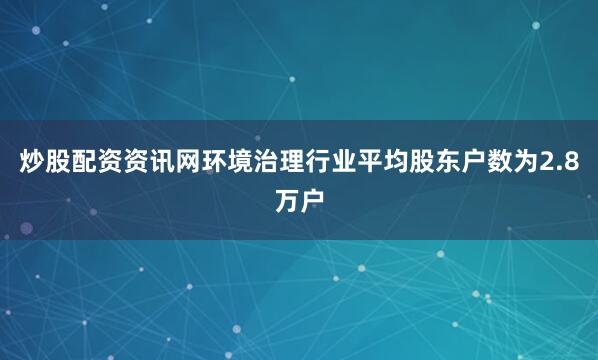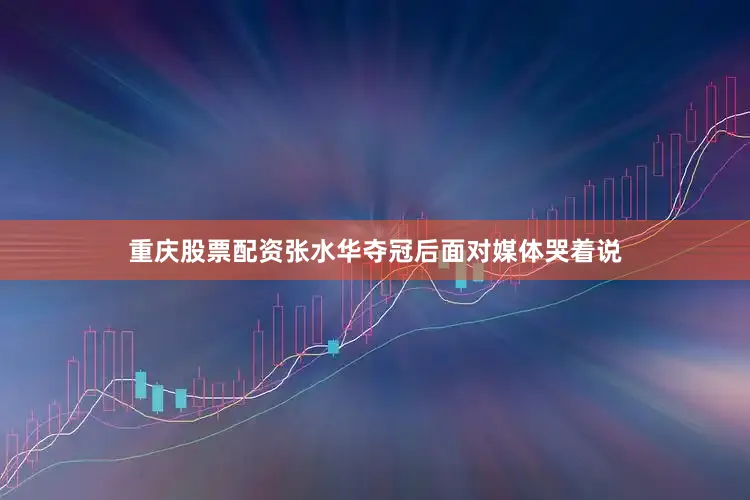题图:歌手易知难,摄影:肖全
我从来不会怀念任何年代,
我觉得现在挺好。
——芒克
回不去了
文 | 赵原野
来源 | 最人物
01
回到久远的八十年代,北岛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号,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,冯骥才住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……他们的家不过几站公交车的距离。
那时,一壶酒就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,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与单纯。
没有互联网、没有手机,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国外诗集,蹬着三轮车就聚到了一起,坐在路灯下的马路边,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诗歌。
展开剩余95%以北岛、海子、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们,在激情澎湃的时代,将自己的生命与理想无所保留地投进了诗歌中。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,“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就十分美好”。
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,见证着80年代初文学青年掀起的热潮。
1973年,芒克写下那句著名的诗句:
太阳升起来,
天空血淋淋的,
犹如一块盾牌。
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,
没有人来问我,
没有人宽恕我。
年轻时的芒克
那年,顾城开始学习画画,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。
期间,他回到北京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、借调编辑,在《北京文艺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报刊零星发表过作品。
1977年,顾城在《蒲公英》上发表诗歌,引起剧烈反响,之后与江河、北岛、舒婷、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。
顾城
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,
我想擦去一切不幸,
我想在大地上,
画满窗子,
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。
写作的人是敏感的。
在顾城写下孩童般纯真的诗句时,远在安徽怀宁县的海子,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。
那年,他才19岁。
如此年轻便成为大学老师,这样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个年代的“成功人士”,然而海子偏偏喜欢写诗。在学校,他是出了名的固执,从不参加活动与会议,独来独往。
海子
“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,和物质的短暂情人”,浓烈的孤独、明亮的真实,海子是一个过于纯粹的诗人。
在政法大学,他的工资被扣到所剩无几,还要挤出钱来给老家的父母与弟弟。
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丰富,反复拉扯着敏感脆弱的海子,他逼仄的屋子里,只有一张桌子、床与收录机。
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
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
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
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
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”
这个热烈而悲凉的天才诗人,最终选择在冰冷的铁轨上告终生命。
没人知道,当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近时,他的脑海中呈现了怎样的画面。他或许在想念自己爱人的脸,他或许根本不屑回望那个精神贫瘠、鸡零狗碎的工业社会。
那年,海子才25岁,他最后的遗言非常简短:
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,我叫查海生,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。
02
回想1986年12月,为了庆祝《星星》创刊30周年,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“中国·星星诗歌节”。
北岛、顾城、谢烨、舒婷……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们纷纷前来,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,也是最后一次。
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,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,那一张张动人的脸得以留存。
1986年星星诗会,由左到右:舒婷、北岛、谢烨、顾城、李刚、傅天琳
“肖全,我认识你那么久了,你还没给我拍过一张照片。”讲这话的人,是易知难。
1990年,成都。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给杂志写崔健的解说词,一回头,看见易知难倚靠着钢琴在抽烟,神情忧伤,不一会儿眼睛里就满是泪水。
肖全并没有与她交流,也不知她的悲伤从何而来,只是将那个瞬间拍了下来。
易知难 1990年5月 肖全摄
因为这张黑白胶片,易知难走红于成都文艺圈,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可替代的气质,清楚区别于周围其他人。
后来的她销声匿迹,人们都在找她,反复试图寻找易知难的消息。面对想要打探自己平静生活的外界,她只说了四个字:“今昔何惜。”人们所追逐的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难,如今她已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,松开了紧皱的眉,一切都过去了。
除了易知难,肖全镜头下还有一个著名女人——三毛。
那个为了爱情远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,1990年9月,三毛从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几天,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时间,在成都老巷子拍了这个自己仰慕许久的传奇女作家。
拍完照后,她随性地说了句:“咱坐三轮车回去吧。”
三毛是个极度浪漫的人,她曾说:
很多年以后,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,我也偶然想起了你,我们去看星星。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,好像铃铛一样。
三毛与肖全
1991年1月4日,肖全拍完三毛4个月后,三毛自杀了。
她没有留下遗书,没有留下只言片语,她的生命永远留在了48岁。
经历过人生种种境况,才知道生活的卑鄙与残暴,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重重迷雾中,纷纷觉醒,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朦胧派诗人莫属北岛。
对痛苦格外敏感的北岛,也许受其父亲影响最大。
北岛的父亲赵济年算得上半个文化人,是茅盾、张恨水、鲁迅的书粉,可见其读书种类之杂。从《红旗》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到《电影艺术》《俄语学习》《曲艺》和《无线电》,可见爱好之广。
北岛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,自然成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,父亲是他文学记忆的起点。
年轻时的北岛与父亲
物质与精神同样饥饿的少年时期,试图反抗秩序的文革时期,也一直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。
1969年,北岛高中毕业后,到北京城建公司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,过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。直到1970年春天,当北岛和几个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,有位朋友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,给他强烈的震撼,随后开始写诗。
在正式写诗前,他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,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灯塔、岛屿、船只的意象。
悲哀的雾
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
在房子与房子之间
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
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
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
一只只疲倦的手中
升起低沉的乌云
在北岛离开建筑工地时,好友芒克来到白洋淀插队,次年也开始写诗。
1976年,芒克回到北京,两年后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《今天》,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,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。
北岛是民国生人,芒克是新中国生人。两代人,就差一岁。
两人的笔名,极具戏剧性。
芒克的笔名是北岛起的,因单薄的外表,绰号“猴子”,便起了 Monkey 的谐音字。
北岛的笔名是芒克起的,两人有次在晚上骑自行车,芒克想起北岛是南方人,但一直生活在北方,那时北岛出了一本诗集《陌生的海滩》,里面多次出现小岛,最后取笔名“北岛”。
好友二人先后把《今天》杂志贴在各大文学报社的门口,还有各大高校。
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负责这件事的,是入学不久的陈凯歌。
陈凯歌,1986年,肖全摄
那年秋天,北岛与芒克创立文学刊物《今天》,一个全身落满黄土尘末,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,脸庞黝黑的年轻人,走进了西安建国路71号院的《陕西文艺》。
他是从延安大学前来报到的路遥。
路遥
03
路遥自小生活在一贫如洗的家庭环境中,衣衫褴褛,贫瘠的生存窘态,让他不敢走到人前。食不果腹、被人讥笑,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痛苦的记忆。如此困顿的经历,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主题,始终围绕着农村的知识青年,如何生存的故事。
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,路遥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
大家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身上,看见黄土高原的土气背后,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。1977年,《陕西文艺》恢复了刊名“延河”。
路遥有机会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导,他通过文章《病危中的柳青》和《柳青的遗产》,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。在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,路遥多次为柳青扫墓。有一次,他在前辈的墓前辗转多时抽烟沉思,突然跪在墓碑前,失声痛哭。
那一刻,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1978年,路遥创作了六万字的中篇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,寄到各大刊物纷纷被退回,最后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经历。
路遥心生绝望,想把自己写的稿子烧掉,万分挣扎后,他最后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,心绪极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,就付之一炬。
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。
没几天,路遥就接到了全国发行量最高的《当代》独具慧眼的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。
秦兆阳热情肯定其创作的同时,指出其不足,与他商量:可以就此发表,但如果愿意修改,请到北京。
路遥背起行囊,来到北京,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,做了认真的修改。
1980年秋天,修改后的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发表在《当代》1980第三期,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这极大地提升了路遥创作的自信,他曾说:
我几十年在饥寒、失误、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,苦苦追寻一种目标,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。
同年秋天,史铁生肾衰竭初发,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,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。
地坛的路面上,留下过无数的轮椅压痕。
史铁生
曾有人问史铁生,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。
他认真思考后,回答:“走投无路沦落至此。”
这不是自谦使然,21岁那年,史铁生提前起进入人生的暮秋——他的腿,不能走路了。
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,躺着从医院出来,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,差点要跟大夫打架。
当年下乡插队时,他只是感到腰部阵痛,吃了药物拖延着。回到北京前,史铁生与好友一同登上了华山,这也许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壮举。
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“透析”的未来,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。
04
两腿初废时,史铁生曾暗下决心: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,哪儿也不去了。
可等到有一天,家人劝说着把他抬进院子,一见杨柳和风,他的决心即刻动摇。
之后又有友人们常探望,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,史铁生的心就越发地活了,设想着,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。
路无法再用腿去走,只能用笔去找。
史铁生
1981年,史铁生发表处女作《秋天的怀念》纪念去世的母亲,震惊文坛,他心想: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,就能看到了。
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,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,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......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,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。
之后颇负盛名的《我与地坛》,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。
地坛与他建立了某种关系,史铁生坐在其中,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,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。他的一腔笑意下,尽是爱与真诚,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,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。
史铁生经历人生的转变时,余华在忙着对付别人的牙齿。
这年,是余华做牙医的第五年。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,拔掉了一万颗牙齿。
那无数个张开的嘴巴,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。后来,他在散文里写道: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。
彼时,与无数颗陌生的牙齿打交道的余华,不会想到,14年后,自己的小说《活着》会让导演张艺谋大放异彩,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。
百无聊赖的日子里,他开始写小说,1983年,余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,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《星星》。
这次改稿回来后,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——这样的机会,他梦寐以求了很久,因为可以喝茶、看报。
年轻时的余华
三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,他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,意外读到了卡夫卡。
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,那种带有先锋性质的写作方式,冲击着他的内心。
余华说:
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,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。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。
随后,受卡夫卡影响,26岁的余华完成了处女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文字锋利却不见血,让人直视其筋肉组织。
余华
很快他就赢得了鲁迅文学院的关注,邀请他到创作研究生班学习,并调到了嘉兴文联,当时他的同学中就包括莫言,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。
彼时的莫言已经发表小说《红高粱》,引起文坛轰动。1988年,由张艺谋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《红高粱》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
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十分有趣,自小在农村长大的莫言见到黑黝黝的张艺谋,以为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,顿时心生好感。
我对张艺谋了解了一番,他担当摄影的《黄土地》我很喜欢。
张艺谋与莫言
开拍之前,莫言把剧组的所有人都请到自己家里去,有张艺谋、巩俐、姜文,也有顾长卫。
因为高密农村的一片高粱地,他们聚到了一起。红高粱有特别的语境意义,就算在最贫瘠的土地上,经历多少风吹雨打,都能埋头成长,生生不息。
莫言、姜文、张艺谋三个男人光着膀子合了一张影,巩俐站在旁边笑靥如花。
由左到右:巩俐、莫言、姜文、张艺谋
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,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。
那一年,张艺谋37岁,莫言32岁,巩俐22岁。
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,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。更没有人知道,多年以后,莫言将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。
电影上映后,在当时一张电影票几毛钱的情况下,最后炒到了10元一张。
37岁的张艺谋凭借这部电影,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,一片高密的红高粱连接了他与土地,也让他读懂莫言。
05
1994年,张艺谋又改编了一部经典小说作品《活着》,作者是余华。
他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,向人们展示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惨况。
悲剧接踵而至,令人无法喘息。
在余华的作品里,经常会有血腥、绝望的场面,他一反之前文学世界里的温情脉脉和梨花带雨,而是将悲痛最大化。
张艺谋看中了这部小说里通过福贵一生经历,反映那个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深刻寓意。
最终,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被搬上了国外电影荧幕,取得巨大成功,在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全胜。
电影《活着》剧照
当时只有29岁的巩俐,将朴实的家珍演绎得让人心碎。在她的眼泪与笑容中,我们看见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。
这部电影直接把张艺谋推到了“第五代导演”的主导地位上,让福贵的扮演者葛优成为影帝,也让当时只有33岁的余华名声大噪,他成为先锋派作家的领头人。
在80年代的文坛,总有人将余华与路遥的作品拿出来探讨一番。
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,不同的是余华亲眼看见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,路遥却没那么幸运。
他的创作之路,漫长而崎岖。
06
80年代的文人们在新旧嬗替的变化中的种种面容,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,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,有的已面目全非,有的依然清澈。
2010年的最后一天,史铁生去世了。
距离他60岁生日,还差5天。生前他早已写好遗愿:“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。”
那是一个寒冬,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,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。
左二为顾城,右一为北岛
人随风飘荡,天各自一方。
转眼离创办《今天》刊物杂志过去四十多年了,已75岁的芒克不是个怀旧的人,也不再写诗,面对想要窥探80年代的后生,他说:
我从来不会怀念任何年代,我觉得现在挺好。
发布于:江苏省盛达优配官网-配资十大平台-可靠股票配资网-证券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